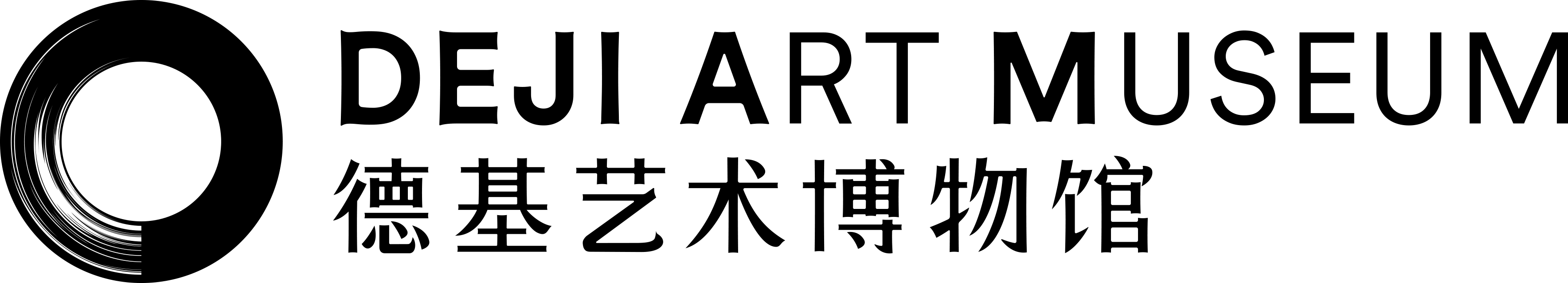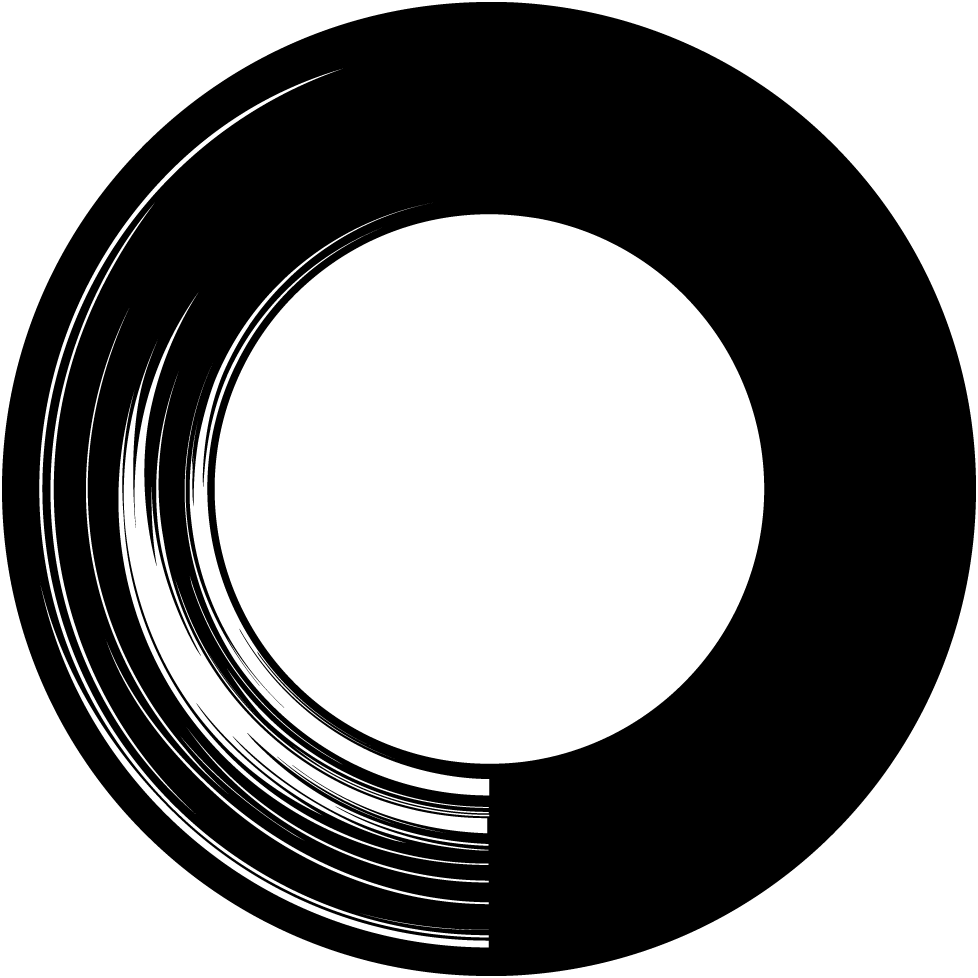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华兹华斯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上大学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禁锢已久的国门洞开,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狂飙涌入,此消彼长,光怪陆离,令我们这些初习绘事的学生目不暇接。当时虽看不懂那些新奇古怪的画面,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激情在涌动,于是疯了般画了许多很“现代”的油画。日子久了反觉空荡荡的,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这样做的意义。于是,心中慢慢萌生出一个疑团:绘画是什么?我为什么绘画?那是我最早对于艺术的思考。
绘画是什么?绘画的意义何在?似乎是个不着边际的话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也许没有人能说得清。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否则,我绘画便毫无意义。带着这个疑虑,我请教过许多人,也试图通过阅读找到答案,结果都很失望。后来逐渐明白,这个命题别人无法帮你,必须由自己来解答。此后我便不再盲从于新潮的艺术流派,也不被新奇眩目的艺术形式所诱惑,而是沉静下来体验生命,倾听自己的心声,并将这种心声幻化为胸中的意象,再通过视觉形象创造呈现出来。
从1986年至今,我的艺术活动基本在这种状态中持续进行。许多作品随着我生活的旅程迁徙自然而成,尽管存有缺陷,却是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映射,是寻常生活中的片段感悟或是深藏意识底层的影像。它们经大脑酝酿、剪裁、编织而成,其基础是流动的意识与凝固的情感,是心灵深处抽象意识的外化。
绘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环境以及现实语境下有着不同的现实功能与精神指向,艺术史的书写与评价角度也各不相同。绘画对每个艺术家来说也有不同的意味与含义。2017年,我在太原郊外30公里北齐徐显秀墓室里,借助考古队微弱的灯光仔细观摩甬道双壁和主墓室墙面的壁画,我的眼光倘佯在那些出行仪仗队列中英姿勃发青年人的脸上,心里在想当年那些画师的模样,他们的身世、家庭、性格和才气,也许他们是被请来的民间画师抑或是北齐时期赫赫有名的宫廷画家。在漫长的历史图景中,绘画被赋予了不同的人文内涵与当下现实需要。对欧洲许多古典画家来说,绘画就是一门手艺,一门和其他谋生手艺一样可以养家糊口的技能。不管是服务于皇家、宗教或贵族的宫廷御用画师,还是在市井开店的画家,他们本质都是要依靠客户订单才能生存下去。中国古代还有些酷爱绘画的人,他们是社会文化精英士大夫阶层,他们不以绘画为生而是以此来消解精神困境,诚如罗樾所说“绘画成了一种修身养性和彼此沟通的工具或是一种人文锤炼”。几百年来,他们创造了许多杰出的中国文人画经典,他们是我艺术上的精神导师。
绘画对我而言是一种探究人生意义的途径,抑或是能将自己摆渡到人生彼岸的小舟。我将绘画当作自己参悟的必修课程,绘画便是参悟,绘画的过程就是对自己内心的探究、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的解读。我希望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可见的第一自然洞见不可见的第二自然,能超越有限之后的无限。当绘画不再承载图像纪录或再现浅表的生活情境,摆脱功利目的时,便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和更宽阔的文化意义。正如德波顿在《拥抱似水年华》中所说:“绘画的美感和绘画中所表现的内容无关。”在绘画中,那些线条、色彩、材料、肌理混合着艺术家特有的手工痕迹将艺术家的思绪凝合为可视的画面图像,从而完成物质到精神的转换,它的美源自艺术家内心对事物的认知和真实情感的显现。
我希望自己的艺术能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跨时代,能经历时间和陌生文化语境的考验,能让人一眼读懂并为之心动。我无需挪用泛滥的社会符号、标签式的传统文化资源讨好市场与观者,而以视觉艺术方式关怀人类的共性以及人性深处最柔软、最需温情的部分,将人们从现实困境中抽离出来,进入无我之境,充分感受生命的存在和万物之美。
我相信“艺术是什么”以及“艺术于我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对于每个艺术家都有不同的答案。艺术正如“美”一样,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艺术”在每个人生活中有不同的含义。木心曾发问过:“艺术品分三大类:一、有现实意义,没有永久意义。二、有永久意义,没现实意义。三、有现实意义,有永久意义。”我欣赏那些不朽的艺术经典,它们不受文化、地域、时间的阻隔,能永久地打动人心,那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样的艺术经典是我毕生的追求。
当然,我们对艺术的认知是渐进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艺术有不同的看法,艺术与生命的含义随着我们心智生熟而发生微妙的变化。莎士比亚在《麦克白》第五幕有过“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经典台词。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而且也没有意义,就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都无意义。”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人生有无意义这个哲学谜题,才使得我们在无意义中去找寻意义,才使得我们在艺术中忘情地工作,从而得以解脱生命的困境,或许这就是艺术的真谛。
2018年中秋